作者:梦中梦789
2025/12/25发表于:001
是否首发:是
字数:8,346字
北陵夜话,下半章
1946年公历1月,我送走了美国技术调查团的最后几个成员,由于国军暂时还
需要仰仗美国提供一些帮助,上级便让我继续以联络官身份留在美国驻沈阳领事
馆,做一些协调方面的工作。我和胞弟云卿又有了几次私下接触,在他指引下,
我抽空回老家给老父母扫墓祭拜了一次,然后便觉得此生心愿已了,可能再不会
回到这里了。
让我意外的是布伦希尔德主动来沈阳找我,她告诉我英国政府已经把之前扣
下的她几年的薪水一次付清,又给了少量补偿,既然手头宽松,她就想到主动来
找我,她还提出想要来和我同住,这倒是问题不大,她的到来在美国领事馆里还
引发了一场持续几天的小小风波。
驻华美军里据说已经有上千人都娶了中国女人做战争新娘,其中最著名就是
陈纳德将军的夫人,陈香梅。这里自然也有不少,娶中国女人的美国人多了,难
免在社交场合会互相攀比,比比谁娶的中国新娘出身更高,肤色更白,英语说得
更好什么的,满足一下男人的虚荣心。
而布伦希尔德,一个金发,高挑的白人女人,论气质长相都不输给这里任何
从美国本土来的白人女人,至于她的丈夫我,被认为暂时可以忽视。美国领事馆
的白人都认为,我能娶到一个白人女人这种事,应该只是她说的一个笑话,过不
了几天这个白人女人,就会和很多欧洲的女人一样拜倒在美国梦里,解放欧洲的
美军,从英、法、德、意、等国都能娶回很多女人,拿下她也是可预期的小意思。
于是想要追求她的美国男人纷纷各展本事,我对此完全没有任何应对之策,
甚至觉得反正娶她也是我捡的一个天大的便宜,如果上帝要把这份幸运从我手里
收走,我也没什么可抱怨的,以前睡过她,可能就够了,不应该贪心的以为她真
会把我当回事。
但布伦希尔德却完全对这些她眼里油腔滑调的花花公子不感兴趣,好几次把
送来的鲜花扔在地上再踩几下。后来干脆披上黑纱,说是给自己在欧洲阵亡的哥
哥们服丧,把所有她眼里品行低劣的美国暴发户子弟拒之门外。
有一个和我比较交好的黑人警卫善意地告诫我,不要和我的白人夫人一起出
门,也不要两人并行,要保持适当距离,当然在自己房间里只要拉上窗帘,那别
人管不着,但也别闹出大的声响。
我对这套种族秩序的暗规早就熟悉,我感谢了他的好意,并问起了他的家人,
这个黑人警卫说,他老婆在这里做帮厨,女儿作为女仆正和一个海军陆战队的小
伙子交往,在这里服务的黑人都很希望把自己女儿嫁给白人,觉得那样的话以后
的日子会好过不少。
在沈阳城里闲逛时,我还遇到过几次,苏联兵拿着罐头和烟草等物敲开中国
女人的家门,有一次还看到一个苏联军官在和他的中国情人道别时,惭愧地说:
苏联不让他们带资本主义国家的女人回去,所以没办法向她保证些什么。
这几天一个朋友告诉我,上级得知我娶了一个洋女人,认为我已经完全被美
国收买,不值得再被信任,好在过不了好久就可以完全摆脱我了。我对这个结果
并不意外,只是等闲视之。随着更多国军的到来,黄历新年也在临近,城里民间
自发的节日气氛越来越浓,苏联对城区的管控也相应放松,以避免引起不必要冲
突。我和胞弟云卿约定在黄历新年夜,一起便装去找个妓院过节庆贺。到了那天,
妓院和饭店自然都是生意最红火的,人流一多我们兄弟的相遇也就不容易被人注
意到,布伦希尔德也穿着男装非要跟来,她说就当是长长见识吧,我拗不过她,
只好同意,但让她在外人面前少说话。
几张美元和卢布摆到桌面上,妓院的老妈妈马上眼前一亮,说有两个关内刚
拐卖来的丫头,还是女学生来着,甚是惹人怜爱,要不是看在我们是给友邦工作
的,她还舍不得拿出来这等水灵的好货。说着招呼人去收拾好房间,还张罗从隔
壁酒楼置办了一桌好菜,说是让我们稍等一会儿,酒菜会和两个姑娘一起送来。
这个老妈妈以为是布伦希尔德带我们来的,便把手里身材最丰满,个子最高
的女人叫出来,让她挑选,布伦希尔德看了几个,都觉得太矮小了,不够味,便
询问老妈妈有没有白人女人在这里做妓女的。
这个老妈妈连忙赔不是,说起现在苏联把各地的白俄都抓起来了,她也不敢
私藏,至于别的白人女人,她是见都没见过。布伦希尔德于是推说酒醉,这次就
先不要姑娘了,但要在这里好好洗个澡,老妈妈马上又安排人去忙活。
听老妈妈这么说,我也长舒了一口气,我猜布伦希尔德刚才问的,就不像真
想找姑娘的样子。等进了屋,我用德语问她刚才怎么想的。
布伦希尔德冷笑一下,也用德语回答我:如果我发现这里有白人妓女,卖身
给中国男人,那我就先杀了她,然后我自杀给她偿命。
我问起胞弟和他的苏联妻子伊莲娜的事,胞弟说,已经离婚,反正早晚如此,
不如早离,伊莲娜现在正和一个苏联军官交好,要不也想带来认识一下。
我们几人正闲聊着,走进来两个穿着蓝色旗袍,女学生打扮的姑娘,她们看
起来入行尚浅,只是低着头不敢看人,两人都自称本也是清白人家,都是因为父
亲被恶友所骗,一个在北平齐老爷手下进了县城的维持会,一个进了南京汪总裁
下令筹办的电影公司,如今父母都被抓起来,也不知判的如何,亲戚嫌弃他们名
声不好,十分碍眼,就卖给拐子,拐子带她们搭上了出关接收的火车,最后流落
到此。
说完都不禁小声哽咽,看起来甚是愁苦,这时一个招呼上菜的老窑姐,上前
给赔不是,说这两个虽不是雏,但新入行不懂规矩,把两个丫头拉出去教训一番,
再进来时,两个丫头只是木讷的假笑,可仍不如别的姐妹,会说些浪话勾搭,却
也别有一番风味。
我们兄弟两个本就为找个说话的地方,对要的什么姑娘并不看重,况且我还
有布伦希尔德珠玉在前,并看不上这等土妞,于是一味劝酒,不多时将两个丫头
灌醉昏睡过去。
在那个新年的晚上,我们兄弟说了很多这些年的生活,也喝得断片了,醒来
时记不清到底都聊了什么。黄昏我醒来时,我看到胞弟正操着其中一个还在昏睡
的姑娘,他问我要不要和他一起,我说不必了,我这个也给你,我还得留着回去
交公粮,云卿胞弟笑着说,那他可就不客气的一马双跨了,我笑着赞许他身体真
好,云卿说:不过是及时行乐罢了。在乌苏里江水面迫降时,自己往外吐了好几
口血,苏联医生检查后说,迫降时的冲击可能压坏了内脏,现在看起来没事,但
难保没留下什么后遗症。我对胞弟说:那你不妨在这里多住几日,最后让老鸨子
给你找个清倌人享受一下。说完我感到一阵头疼,便又趴下睡着了。
等初一上午我再次醒来胞弟和两个丫头还在角落里睡得死沉,而布伦希尔德
已经坐在窗边,穿着昨晚那身男装,外套却脱了,只剩一件贴身的羊毛衫,勾勒
出她高挑而有力的身形。她没说话,只是冷冷地笑着,那种笑带着一点残酷的玩
味,像猫终于等到了老鼠自己钻进陷阱。
她慢慢走过来,脚步很轻,却让整个房间的空气都绷紧了。
「怎么,是我的魅力不够大吗?」
她用德语低声问,声音里带着嘲弄,却又藏着真正的怒意和不安。
「还是你们中国男人,都喜欢那种小小软软,哭起来像小动物一样的女人?」
我酒还没醒,脑子嗡嗡作响,被她这一逼问吓得一激灵,赶紧低头认错,语
无伦次地跟她往外走。身后老妈妈还在堆着笑脸送客,出了妓院,沈阳的晨风卷
着雪粒扑到脸上,看到街上没什么人,布伦希尔德炫耀式地搂起我的胳膊,这是
个在公开场合很放肆的举动。她时而像老虎,撕咬、暴虐、把我压在身下,踩在
脚底;时而像猫,蜷缩在我怀里,偎依在我腿边。我对她的身体,十分迷恋,里
面带着一点恐惧和自卑,我知道自己配不上她,总觉得她迟早会离开,可越是这
样,越想要抓住。
布伦希尔德预约了另一家旅店,在房间里她拖去外衣和小皮靴后,故意魅惑
的抚摸自己穿着玻璃丝袜的小腿,但并不急于做点什么,而是炫耀的从包里拿出
一瓶高级葡萄酒,她说这是从领事馆一个美国人的办公室里偷来的,她的肤色和
长相就是她在领事馆里最好的通行证,除了涉密部门会阻拦她,其他的美国男人
都对她很谄媚。
布伦希尔德也很享受这样感觉,她说起她在英国时就是这样,堂而皇之的靠
记者身份主动和几个英国年轻军官保持若即若离的亲密关系,必要时也和他们上
床,然后用隐藏的小型相机拍摄她在英军那找到的各种有价值文件,交给接头人。
我很有兴致的听她讲起自己的过往,那是她会终身引以为傲的一段经历,对
她说:「我还以为英国人冤枉你了呢!没想到你是来真的。」
布伦希尔德看着窗外飘落的雪花说:「我是民间身份志愿干这件事,和接头
人也是间接联系,并不见面,我甚至怀疑英国人可能利用我传递了某些假情报,
但我无法鉴别。直到1944年初,英国开始认真考虑反攻欧洲的登陆行动,才把我
流放到印度的阿萨姆战区去,可能因为假情报,也可以反向推测出对方在有意隐
瞒什么吧。」
说着这个布伦希尔德半躺在床上,一双洁白紧绷的长腿紧紧闭合,膝盖半曲,
一双40码的脚丫,像芭蕾舞者一样,在半空中踏着虚空的舞步,然后她看向我红
唇微笑,优雅的拿起床头柜上装在高教杯里的红酒自己喝了一口,舌头轻轻舔了
一下嘴边。再假装有些热的,往下拉了拉睡衣,里面是一对丰满洁白的乳房。搭
配上她1米9的纤细而高挑的身材,真是个天生的婊子。
我有理由怀疑,她靠这付勾人的样子,到底和多少英国军官和绅士上过床,
似乎是看出了我心中的疑问,布伦希尔德对我说:「被我算计的男人,没有20,
也有10个,但你是我唯一愿意免费奉送的,而且我愿意为了留住你,不再去过那
种醉生梦死的生活。如你所知的,德国战败了,元首也死了,我,我不知道这世
上还有什么值得我去不顾一切的效忠,和为之而奋斗的了。」
我爬上去,跪在她的脚边,亲吻她的脚趾和脚背,小腿,这真是太美的,我
的双手紧紧搂着她的小腿不停的抚摸着。她也很享受这种被男人伺候的感觉,不
时抽出一条腿来,把脚顶到我的脸上,让我舔她的脚心,然后她就会因为痒痒而
欢快的大笑和试图挣脱,我就会把她的小腿抱的更紧。
我搂着布伦希尔德的优美小腿亲个不停同时,眼睛余光注意到了她床头柜上,
有一个她走到哪就会带到哪的相框,里面是德皇威廉二世手拄军刀的半身像,想
起这个女人只要在床上感到舒服了,就会喊着:嗨!凯瑟。这让我觉得,我只是
个替身,她真正的情人永远是德皇,和那个已经灭亡的德意志帝国。
我们闹了一会儿,布伦希尔德回顾起,1944年初,我们两个在印度,阿萨姆
省的贾布瓦空军基地的相遇。布伦希尔德说:在印度那段时间无疑是她人生中最
难熬的,这种前线地区,和英国本土大为不同。基地里所有英国人,美国人都在
提防她,拒绝她,到处站着背枪警戒的印度土著士兵,她的活动范围大大受限,
多走两步都要打报告,或者等着电话通知。
而且每天无所事事,虽然这里有上百外国记者,但只能通过贾布瓦的英军新
闻处获取信息和转发,此外所有的军用设施,尤其军官办公楼,都被禁止进入。
她的生活水平也大幅下降,以前她缺钱了,随便找个英国或者美国的白人军
官,和他暧昧一下,允许他的搂抱和亲吻,谈谈等战争结束了,我们一起私奔,
男人就会送上大笔金钱和贵重礼物,急不可耐的想在随时会死的情况下,赶紧把
金钱兑换成片刻的肉体欢愉。
但到了真正每天都死人的前线地带,这里官兵找女人,也得先被情报部门审
查背景清白的才行。于是她变得很穷,除了配给的基本生活用品和食品,她什么
也买不起,记者们被安排统一划定居住区域时,别人也不想和她一个帐篷,免得
被她连累。
布伦希尔德平复下心绪后,继续说:「那段时间你是唯一没拒绝我的男人,
而且从你那借钱让我能买得起军营商店里那些烟酒等东西,让我勉强觉得还能活
得下去,不至于向我讨厌的英国人屈服。
而且你是飞行员,我多次看见你冒着飞溅的炸弹碎片跑进飞机驾驶舱,升空
和敌人作战,你的勇气和责任感让我钦佩,我多次听参加过一战德国空军的邻居
说起:空战,不像地面上有墙壁和壕沟可以躲避,敌人也看不到你投降时举起的
双手。在一望无垠的天上作战,飞行员只有要么胜利,要么死去,那是真正勇敢
者才能参加的无畏冲锋,看上去充满了古典式的,骑士精神式的悲壮美感。
而且我还想到了前次大战中的非洲德军的福尔贝克将军,他手下也有黑人士
兵,为他勇敢战斗。所以我就想,就当我被一个够资格的,黄种人蛮族骑士所征
服吧,想多了以后我有一次在梦里居然觉得很刺激,醒来后我手淫觉得这也蛮舒
服的,所以我才觉得作为对你的特别垂青,允许你爬上我的床。
后来44年下半年,你回国作战期间,对我是最难熬的,我身体和心理都适应
了你的存在,你却走了,然后还有传说你死了,等年末再遇到你时,我几乎疯了
一样,发现原来我这么需要你能留在我身边。」
我也想起那段日子,回应布伦希尔德说:「那段时间,正是滇西战役,中国
军队向缅甸发起反攻的关键时期,我被调回国执行对地支援任务,在缅北上空被
日军高炮击落,跳伞后在那片深山的密林里,靠当地傣人土司和汉人马帮的救助,
走了几个月才回到友军的防区,然后在医院里又躺了1个多月才恢复过来,回到印
度的空军基地继续作战。我不敢相信我还能遇到你,于是我也疯了一样想要抓住
你,不让你跑了。」
布伦希尔德的眼睛在昏黄的灯光下闪烁着,那是一种混合了回忆的温柔和当
下欲望的野性。她伸出双手,交叉着搁在胸前,那姿势像是在邀请,又像是在挑
衅。我的心跳一下子加速了,我们做爱这么多次,我早就摸透了她的肢体语言。
她伸出一只脚,就是想让我跪下来亲吻她的脚趾,舔她的脚心,让她像女王一样
掌控一切;但双手交叉伸出,这他妈的就是在求我粗暴地对待她,像强奸一样征
服她这个高傲的日耳曼婊子。她知道我爱她这副贱样,也知道我每次都忍不住满
足她。
我咽了口唾沫,酒劲儿还没完全散去,脑子里嗡嗡的,但下身已经硬得像铁
棍。她的长腿还半曲着,玻璃丝袜包裹下的小腿曲线完美得像艺术品,我爬上床,
跪在她身边,先是抓起她的手腕,粗鲁地扭到背后。她没反抗,反而笑出声来,
那笑声低沉而沙哑,带着德国口音的嘲弄:「来啊,黄皮猪,来试试你这小鸡巴
能不能让我叫出声。」
「闭上你的贱嘴,布伦希尔德。」我抽出她睡衣上的布腰带,我用力一拉,
把她的双手捆在身后,她的身体微微前倾,丰满的乳房从睡衣里晃荡出来,粉红
的乳头硬得像两颗樱桃。我扇了她一耳光,不重,但够响亮,她的脸上顿时泛起
红印,她舔了舔嘴唇,眼睛里闪着兴奋的火光:「就这?蒙古杂种,你他妈的就
这点力气?」
她的辱骂像火上浇油,我的心底涌起一股扭曲的快感。这女人,总爱在床上
把我当靶子,骂我是黄种矮子、亚洲蛮子、配不上她的日耳曼血统。可她越骂,
我越想操烂她,让她这张傲慢的嘴只能发出浪叫。我抓起她的头发,把她脸按到
枕头上,她的长发散开,像金色的瀑布,我另一只手伸到床下,从她的行李里翻
出那根马鞭,她说她以前在阿根廷的牧场里常会骑马牧牛,所以一直带着这个指
望在外面也能有机会骑马,后来我发现用来抽她屁股也很合适。
「婊子,你不是喜欢玩儿这个吗?」我冷笑着,扬起鞭子,抽在她翘起的屁
股上。啪的一声脆响,她的身体一颤,屁股上立刻浮现一道红痕。她扭过头,吐
了口唾沫:「操你妈的,黄猴子!抽啊,使劲抽!老娘的屁股可不是给你这种劣
等种舔的,是给我皇威廉,凯瑟陛下骑的!」
凯瑟,又是凯瑟。她在床上一激动就喊这个称呼,搞得我像个替身一样。但
我没停手,鞭子一次次落下,抽在她白皙的臀肉上,红痕交织成网,她的长腿乱
蹬,丝袜被汗水浸湿,贴在皮肤上更显光滑。她的叫声从低沉的哼哼变成尖利的
浪叫:「啊!贱货!你这亚洲猪!抽死我啊!老娘的屁股是日耳曼的骄傲,你他
妈配碰吗?」
我扔掉鞭子,双手掰开她的屁股瓣,那粉嫩的菊花和湿漉漉的阴户暴露在空
气中。她已经兴奋的流水了,真他妈是个天生的贱货,阴唇肿胀着,晶莹的液体
顺着大腿内侧滑落。我的鸡巴硬得发疼,龟头直顶在她屁眼上,先是用力磨蹭,
我抓起枕头下的套子带上,伸进她的臭嘴里,用她自己的口水给我戴套的鸡巴润
滑,然后对着她的屁眼,一点点挤进去,真是又紧又舒服。「你这日耳曼母马!
现在还不是被我这黄种矮子骑在身下?张开你的贱屁眼,让我操进去!」
她尖叫着扭动:「不!滚开,你这蒙古杂种!老娘的屁眼是给白人贵族操的,
不是你这种黄皮猪!啊——!」我不管那么多,一挺腰,鸡巴生生捅进她的屁眼,
紧窄的肠道像火热的套子裹住我,她的身体猛地弓起,双手在身后挣扎着皮带的
束缚。痛楚和快感让她脸扭曲,泪水混着汗水滑落:「操!疼死老娘了!你这畜
生!拔出去!啊……黄猴子……操深点……不,滚!」
我开始抽插,粗暴地撞击她的屁股,每一下都顶到最深,她的叫床声断断续
续,夹杂着德语的咒骂,我听不懂,但知道她在骂我黄种矮子。我扇着她的屁股,
加快节奏:「叫啊,母狗!你的凯瑟呢?怎么不来救你这贱货?老子操烂你的日
耳曼屁眼,让你知道谁才是你的主人!」
她喘息着,屁股不由自主地往后迎合:「凯瑟……嗨,凯瑟……不,你……
你这矮子……操我……操死我……」她的声音越来越软,身体在我的撞击下颤抖,
我拔出鸡巴,套子上沾满她的肠液,我退下用过的套子,无套的鸡巴直接转战她
的阴道。那里更湿更热,我一捅到底,龟头撞上她的子宫口,她尖叫一声,整个
人瘫软下来:「啊!鸡巴……你的鸡巴……黄种的鸡巴……插进老娘的优等人的
子宫里了……真恶心!你这蒙古杂种!」
我骑在她身上,像野兽一样狂干,双手捏着她的奶子,拧她的乳头,她的长
腿缠上我的腰,丝袜摩擦着我的皮肤,带来阵阵酥麻。房间里回荡着啪啪的肉体
撞击声和她的浪叫:「操我!扇我!黄皮猪,你他妈的就这点本事?老娘在英国
时……啊!深点,操到子宫里,蒙古贱种!」
「闭嘴,婊子!」我吼着,鸡巴在她的阴道里搅动,抽插得汁水四溅,她的
阴唇被我操得外翻,红肿不堪。我又抽了她屁股几下,留下新的掌印:「你这日
耳曼骚货,嘴上骂我,心里却浪成这样?你的凯瑟操过你这么狠吗?老子要射进
你的子宫,让你怀上黄种的种,毁了你的优等血统!」
她大笑起来,笑声中带着哭腔:「射进来!你这劣等猪!老娘的子宫才不稀
罕你的低等精液……啊!要来了……操死我……凯瑟……不,你……我要你……」
她的身体突然绷紧,阴道剧烈收缩,裹着我的鸡巴像要挤干我。她高潮了,尖叫
着:「嗨!凯瑟!哦,奥丁啊……黄猴子……操我……我爱你……」
我也没忍住,猛地一顶,精液喷射进她的深处,她的身体抽搐着,我们同时
瘫软下来。她扭过头,红唇贴上我的脸,亲吻得又猛又急:「我要你……现在我
只要你……跟老娘回家吧,别让我一个人。」
她的吻带着咸涩的泪味,我的心软了,解开她手上的皮带,抱紧她高挑的身
体。她的长腿缠着我,乳房压在我的胸口,我们就这样纠缠着,汗水混在一起。
她喃喃着:「或者哪儿都行……只要跟你……别扔下我这日耳曼母狗。」
布伦希尔德休息片刻,爬起来把偷来的那瓶红酒喝了大半,脸颊飞起两抹羞
红,她懒洋洋地倚在床头,全身赤裸长腿交叠。她用脚尖挑起我的下巴,迫使我
抬头看她。
「告诉我,」她低声问,声音里带着酒意和一丝罕见的柔软,「你真的要跟
我走?离开中国?」
我平静的说:「我已经没什么可留恋的了。父母的坟我拜过了,弟弟选了他
的路,军队也要踢开我这块旧石头。不如干脆去你父亲在巴塔哥尼亚的那片旧庄
园。」
她盯着我看了很久,蓝灰色的眼睛里第一次没有了玩味和审视,只有一种近
乎孩子般的认真。
「可你知道吗?」她轻声说,「我其实很怕,我怕你有一天会后悔,我听说
中国人都很爱自己的家乡的土地。」
我爬上床,把她揽进怀里,闻着她身上混杂着红酒、烟草和淡淡汗味的香气:
「我也怕。我怕我配不上你,但我更怕的是,如果现在放手,我这辈子都不会再
有勇气去爱任何东西了。」
她忽然笑了,那笑声先是低低的,像雪地里远处的狼嚎,然后越来越大,带
着一点歇斯底里。她翻身把我压在身下。「那就别放手。」她咬着我的耳朵,声
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今晚不许想明天,不许想中国,不许想德国,不许想战争
结束后的全世界。就想我,只想我。」
布伦希尔德转过身去跪下,把自己的骚逼对我眼前,用自己的小嘴把我的鸡
巴,用她的小嘴舔的又硬了起来,然后再次转身跨坐在我身上,自己伸手扶着,
把我的鸡巴对准她的阴道口,慢慢坐了下去,开始自己上下活动,像个海妖一样,
要把我彻底榨干,但也让我舒服的欲仙欲死,这个娘们太刺激了。
几夜激情过后,我们都好好休息了几天,直到正月十六,国府的裁军遣散通
知和退休补助一起送到,我和美国领事馆申请后,计划和布伦希尔德一起搭乘美
国的邮政飞机,从北陵机场飞往天津,再转船去美洲。从北陵机场起飞时,我最
后看了一眼东北这片土地,今生我将永无机会再回来了。
……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把我养大的祖父给我看的,可能是我父亲的人的私人笔
记,我不确定这个中国飞行员和布伦希尔德是不是真是我的亲生父母,但学校里
的人都说我有一种中国式的好学和勤恳。
当我追问后来发生的事时,祖父告诉我,他们两人在农庄住了没多久,就把
我留下,两人一起化名参加了阿根廷的南极科考队,死于突然降临的暴风雪中,
只有尸体被发现后运回安葬。
全文完
2025/12/25发表于:001
是否首发:是
字数:8,346字
北陵夜话,下半章
1946年公历1月,我送走了美国技术调查团的最后几个成员,由于国军暂时还
需要仰仗美国提供一些帮助,上级便让我继续以联络官身份留在美国驻沈阳领事
馆,做一些协调方面的工作。我和胞弟云卿又有了几次私下接触,在他指引下,
我抽空回老家给老父母扫墓祭拜了一次,然后便觉得此生心愿已了,可能再不会
回到这里了。
让我意外的是布伦希尔德主动来沈阳找我,她告诉我英国政府已经把之前扣
下的她几年的薪水一次付清,又给了少量补偿,既然手头宽松,她就想到主动来
找我,她还提出想要来和我同住,这倒是问题不大,她的到来在美国领事馆里还
引发了一场持续几天的小小风波。
驻华美军里据说已经有上千人都娶了中国女人做战争新娘,其中最著名就是
陈纳德将军的夫人,陈香梅。这里自然也有不少,娶中国女人的美国人多了,难
免在社交场合会互相攀比,比比谁娶的中国新娘出身更高,肤色更白,英语说得
更好什么的,满足一下男人的虚荣心。
而布伦希尔德,一个金发,高挑的白人女人,论气质长相都不输给这里任何
从美国本土来的白人女人,至于她的丈夫我,被认为暂时可以忽视。美国领事馆
的白人都认为,我能娶到一个白人女人这种事,应该只是她说的一个笑话,过不
了几天这个白人女人,就会和很多欧洲的女人一样拜倒在美国梦里,解放欧洲的
美军,从英、法、德、意、等国都能娶回很多女人,拿下她也是可预期的小意思。
于是想要追求她的美国男人纷纷各展本事,我对此完全没有任何应对之策,
甚至觉得反正娶她也是我捡的一个天大的便宜,如果上帝要把这份幸运从我手里
收走,我也没什么可抱怨的,以前睡过她,可能就够了,不应该贪心的以为她真
会把我当回事。
但布伦希尔德却完全对这些她眼里油腔滑调的花花公子不感兴趣,好几次把
送来的鲜花扔在地上再踩几下。后来干脆披上黑纱,说是给自己在欧洲阵亡的哥
哥们服丧,把所有她眼里品行低劣的美国暴发户子弟拒之门外。
有一个和我比较交好的黑人警卫善意地告诫我,不要和我的白人夫人一起出
门,也不要两人并行,要保持适当距离,当然在自己房间里只要拉上窗帘,那别
人管不着,但也别闹出大的声响。
我对这套种族秩序的暗规早就熟悉,我感谢了他的好意,并问起了他的家人,
这个黑人警卫说,他老婆在这里做帮厨,女儿作为女仆正和一个海军陆战队的小
伙子交往,在这里服务的黑人都很希望把自己女儿嫁给白人,觉得那样的话以后
的日子会好过不少。
在沈阳城里闲逛时,我还遇到过几次,苏联兵拿着罐头和烟草等物敲开中国
女人的家门,有一次还看到一个苏联军官在和他的中国情人道别时,惭愧地说:
苏联不让他们带资本主义国家的女人回去,所以没办法向她保证些什么。
这几天一个朋友告诉我,上级得知我娶了一个洋女人,认为我已经完全被美
国收买,不值得再被信任,好在过不了好久就可以完全摆脱我了。我对这个结果
并不意外,只是等闲视之。随着更多国军的到来,黄历新年也在临近,城里民间
自发的节日气氛越来越浓,苏联对城区的管控也相应放松,以避免引起不必要冲
突。我和胞弟云卿约定在黄历新年夜,一起便装去找个妓院过节庆贺。到了那天,
妓院和饭店自然都是生意最红火的,人流一多我们兄弟的相遇也就不容易被人注
意到,布伦希尔德也穿着男装非要跟来,她说就当是长长见识吧,我拗不过她,
只好同意,但让她在外人面前少说话。
几张美元和卢布摆到桌面上,妓院的老妈妈马上眼前一亮,说有两个关内刚
拐卖来的丫头,还是女学生来着,甚是惹人怜爱,要不是看在我们是给友邦工作
的,她还舍不得拿出来这等水灵的好货。说着招呼人去收拾好房间,还张罗从隔
壁酒楼置办了一桌好菜,说是让我们稍等一会儿,酒菜会和两个姑娘一起送来。
这个老妈妈以为是布伦希尔德带我们来的,便把手里身材最丰满,个子最高
的女人叫出来,让她挑选,布伦希尔德看了几个,都觉得太矮小了,不够味,便
询问老妈妈有没有白人女人在这里做妓女的。
这个老妈妈连忙赔不是,说起现在苏联把各地的白俄都抓起来了,她也不敢
私藏,至于别的白人女人,她是见都没见过。布伦希尔德于是推说酒醉,这次就
先不要姑娘了,但要在这里好好洗个澡,老妈妈马上又安排人去忙活。
听老妈妈这么说,我也长舒了一口气,我猜布伦希尔德刚才问的,就不像真
想找姑娘的样子。等进了屋,我用德语问她刚才怎么想的。
布伦希尔德冷笑一下,也用德语回答我:如果我发现这里有白人妓女,卖身
给中国男人,那我就先杀了她,然后我自杀给她偿命。
我问起胞弟和他的苏联妻子伊莲娜的事,胞弟说,已经离婚,反正早晚如此,
不如早离,伊莲娜现在正和一个苏联军官交好,要不也想带来认识一下。
我们几人正闲聊着,走进来两个穿着蓝色旗袍,女学生打扮的姑娘,她们看
起来入行尚浅,只是低着头不敢看人,两人都自称本也是清白人家,都是因为父
亲被恶友所骗,一个在北平齐老爷手下进了县城的维持会,一个进了南京汪总裁
下令筹办的电影公司,如今父母都被抓起来,也不知判的如何,亲戚嫌弃他们名
声不好,十分碍眼,就卖给拐子,拐子带她们搭上了出关接收的火车,最后流落
到此。
说完都不禁小声哽咽,看起来甚是愁苦,这时一个招呼上菜的老窑姐,上前
给赔不是,说这两个虽不是雏,但新入行不懂规矩,把两个丫头拉出去教训一番,
再进来时,两个丫头只是木讷的假笑,可仍不如别的姐妹,会说些浪话勾搭,却
也别有一番风味。
我们兄弟两个本就为找个说话的地方,对要的什么姑娘并不看重,况且我还
有布伦希尔德珠玉在前,并看不上这等土妞,于是一味劝酒,不多时将两个丫头
灌醉昏睡过去。
在那个新年的晚上,我们兄弟说了很多这些年的生活,也喝得断片了,醒来
时记不清到底都聊了什么。黄昏我醒来时,我看到胞弟正操着其中一个还在昏睡
的姑娘,他问我要不要和他一起,我说不必了,我这个也给你,我还得留着回去
交公粮,云卿胞弟笑着说,那他可就不客气的一马双跨了,我笑着赞许他身体真
好,云卿说:不过是及时行乐罢了。在乌苏里江水面迫降时,自己往外吐了好几
口血,苏联医生检查后说,迫降时的冲击可能压坏了内脏,现在看起来没事,但
难保没留下什么后遗症。我对胞弟说:那你不妨在这里多住几日,最后让老鸨子
给你找个清倌人享受一下。说完我感到一阵头疼,便又趴下睡着了。
等初一上午我再次醒来胞弟和两个丫头还在角落里睡得死沉,而布伦希尔德
已经坐在窗边,穿着昨晚那身男装,外套却脱了,只剩一件贴身的羊毛衫,勾勒
出她高挑而有力的身形。她没说话,只是冷冷地笑着,那种笑带着一点残酷的玩
味,像猫终于等到了老鼠自己钻进陷阱。
她慢慢走过来,脚步很轻,却让整个房间的空气都绷紧了。
「怎么,是我的魅力不够大吗?」
她用德语低声问,声音里带着嘲弄,却又藏着真正的怒意和不安。
「还是你们中国男人,都喜欢那种小小软软,哭起来像小动物一样的女人?」
我酒还没醒,脑子嗡嗡作响,被她这一逼问吓得一激灵,赶紧低头认错,语
无伦次地跟她往外走。身后老妈妈还在堆着笑脸送客,出了妓院,沈阳的晨风卷
着雪粒扑到脸上,看到街上没什么人,布伦希尔德炫耀式地搂起我的胳膊,这是
个在公开场合很放肆的举动。她时而像老虎,撕咬、暴虐、把我压在身下,踩在
脚底;时而像猫,蜷缩在我怀里,偎依在我腿边。我对她的身体,十分迷恋,里
面带着一点恐惧和自卑,我知道自己配不上她,总觉得她迟早会离开,可越是这
样,越想要抓住。
布伦希尔德预约了另一家旅店,在房间里她拖去外衣和小皮靴后,故意魅惑
的抚摸自己穿着玻璃丝袜的小腿,但并不急于做点什么,而是炫耀的从包里拿出
一瓶高级葡萄酒,她说这是从领事馆一个美国人的办公室里偷来的,她的肤色和
长相就是她在领事馆里最好的通行证,除了涉密部门会阻拦她,其他的美国男人
都对她很谄媚。
布伦希尔德也很享受这样感觉,她说起她在英国时就是这样,堂而皇之的靠
记者身份主动和几个英国年轻军官保持若即若离的亲密关系,必要时也和他们上
床,然后用隐藏的小型相机拍摄她在英军那找到的各种有价值文件,交给接头人。
我很有兴致的听她讲起自己的过往,那是她会终身引以为傲的一段经历,对
她说:「我还以为英国人冤枉你了呢!没想到你是来真的。」
布伦希尔德看着窗外飘落的雪花说:「我是民间身份志愿干这件事,和接头
人也是间接联系,并不见面,我甚至怀疑英国人可能利用我传递了某些假情报,
但我无法鉴别。直到1944年初,英国开始认真考虑反攻欧洲的登陆行动,才把我
流放到印度的阿萨姆战区去,可能因为假情报,也可以反向推测出对方在有意隐
瞒什么吧。」
说着这个布伦希尔德半躺在床上,一双洁白紧绷的长腿紧紧闭合,膝盖半曲,
一双40码的脚丫,像芭蕾舞者一样,在半空中踏着虚空的舞步,然后她看向我红
唇微笑,优雅的拿起床头柜上装在高教杯里的红酒自己喝了一口,舌头轻轻舔了
一下嘴边。再假装有些热的,往下拉了拉睡衣,里面是一对丰满洁白的乳房。搭
配上她1米9的纤细而高挑的身材,真是个天生的婊子。
我有理由怀疑,她靠这付勾人的样子,到底和多少英国军官和绅士上过床,
似乎是看出了我心中的疑问,布伦希尔德对我说:「被我算计的男人,没有20,
也有10个,但你是我唯一愿意免费奉送的,而且我愿意为了留住你,不再去过那
种醉生梦死的生活。如你所知的,德国战败了,元首也死了,我,我不知道这世
上还有什么值得我去不顾一切的效忠,和为之而奋斗的了。」
我爬上去,跪在她的脚边,亲吻她的脚趾和脚背,小腿,这真是太美的,我
的双手紧紧搂着她的小腿不停的抚摸着。她也很享受这种被男人伺候的感觉,不
时抽出一条腿来,把脚顶到我的脸上,让我舔她的脚心,然后她就会因为痒痒而
欢快的大笑和试图挣脱,我就会把她的小腿抱的更紧。
我搂着布伦希尔德的优美小腿亲个不停同时,眼睛余光注意到了她床头柜上,
有一个她走到哪就会带到哪的相框,里面是德皇威廉二世手拄军刀的半身像,想
起这个女人只要在床上感到舒服了,就会喊着:嗨!凯瑟。这让我觉得,我只是
个替身,她真正的情人永远是德皇,和那个已经灭亡的德意志帝国。
我们闹了一会儿,布伦希尔德回顾起,1944年初,我们两个在印度,阿萨姆
省的贾布瓦空军基地的相遇。布伦希尔德说:在印度那段时间无疑是她人生中最
难熬的,这种前线地区,和英国本土大为不同。基地里所有英国人,美国人都在
提防她,拒绝她,到处站着背枪警戒的印度土著士兵,她的活动范围大大受限,
多走两步都要打报告,或者等着电话通知。
而且每天无所事事,虽然这里有上百外国记者,但只能通过贾布瓦的英军新
闻处获取信息和转发,此外所有的军用设施,尤其军官办公楼,都被禁止进入。
她的生活水平也大幅下降,以前她缺钱了,随便找个英国或者美国的白人军
官,和他暧昧一下,允许他的搂抱和亲吻,谈谈等战争结束了,我们一起私奔,
男人就会送上大笔金钱和贵重礼物,急不可耐的想在随时会死的情况下,赶紧把
金钱兑换成片刻的肉体欢愉。
但到了真正每天都死人的前线地带,这里官兵找女人,也得先被情报部门审
查背景清白的才行。于是她变得很穷,除了配给的基本生活用品和食品,她什么
也买不起,记者们被安排统一划定居住区域时,别人也不想和她一个帐篷,免得
被她连累。
布伦希尔德平复下心绪后,继续说:「那段时间你是唯一没拒绝我的男人,
而且从你那借钱让我能买得起军营商店里那些烟酒等东西,让我勉强觉得还能活
得下去,不至于向我讨厌的英国人屈服。
而且你是飞行员,我多次看见你冒着飞溅的炸弹碎片跑进飞机驾驶舱,升空
和敌人作战,你的勇气和责任感让我钦佩,我多次听参加过一战德国空军的邻居
说起:空战,不像地面上有墙壁和壕沟可以躲避,敌人也看不到你投降时举起的
双手。在一望无垠的天上作战,飞行员只有要么胜利,要么死去,那是真正勇敢
者才能参加的无畏冲锋,看上去充满了古典式的,骑士精神式的悲壮美感。
而且我还想到了前次大战中的非洲德军的福尔贝克将军,他手下也有黑人士
兵,为他勇敢战斗。所以我就想,就当我被一个够资格的,黄种人蛮族骑士所征
服吧,想多了以后我有一次在梦里居然觉得很刺激,醒来后我手淫觉得这也蛮舒
服的,所以我才觉得作为对你的特别垂青,允许你爬上我的床。
后来44年下半年,你回国作战期间,对我是最难熬的,我身体和心理都适应
了你的存在,你却走了,然后还有传说你死了,等年末再遇到你时,我几乎疯了
一样,发现原来我这么需要你能留在我身边。」
我也想起那段日子,回应布伦希尔德说:「那段时间,正是滇西战役,中国
军队向缅甸发起反攻的关键时期,我被调回国执行对地支援任务,在缅北上空被
日军高炮击落,跳伞后在那片深山的密林里,靠当地傣人土司和汉人马帮的救助,
走了几个月才回到友军的防区,然后在医院里又躺了1个多月才恢复过来,回到印
度的空军基地继续作战。我不敢相信我还能遇到你,于是我也疯了一样想要抓住
你,不让你跑了。」
布伦希尔德的眼睛在昏黄的灯光下闪烁着,那是一种混合了回忆的温柔和当
下欲望的野性。她伸出双手,交叉着搁在胸前,那姿势像是在邀请,又像是在挑
衅。我的心跳一下子加速了,我们做爱这么多次,我早就摸透了她的肢体语言。
她伸出一只脚,就是想让我跪下来亲吻她的脚趾,舔她的脚心,让她像女王一样
掌控一切;但双手交叉伸出,这他妈的就是在求我粗暴地对待她,像强奸一样征
服她这个高傲的日耳曼婊子。她知道我爱她这副贱样,也知道我每次都忍不住满
足她。
我咽了口唾沫,酒劲儿还没完全散去,脑子里嗡嗡的,但下身已经硬得像铁
棍。她的长腿还半曲着,玻璃丝袜包裹下的小腿曲线完美得像艺术品,我爬上床,
跪在她身边,先是抓起她的手腕,粗鲁地扭到背后。她没反抗,反而笑出声来,
那笑声低沉而沙哑,带着德国口音的嘲弄:「来啊,黄皮猪,来试试你这小鸡巴
能不能让我叫出声。」
「闭上你的贱嘴,布伦希尔德。」我抽出她睡衣上的布腰带,我用力一拉,
把她的双手捆在身后,她的身体微微前倾,丰满的乳房从睡衣里晃荡出来,粉红
的乳头硬得像两颗樱桃。我扇了她一耳光,不重,但够响亮,她的脸上顿时泛起
红印,她舔了舔嘴唇,眼睛里闪着兴奋的火光:「就这?蒙古杂种,你他妈的就
这点力气?」
她的辱骂像火上浇油,我的心底涌起一股扭曲的快感。这女人,总爱在床上
把我当靶子,骂我是黄种矮子、亚洲蛮子、配不上她的日耳曼血统。可她越骂,
我越想操烂她,让她这张傲慢的嘴只能发出浪叫。我抓起她的头发,把她脸按到
枕头上,她的长发散开,像金色的瀑布,我另一只手伸到床下,从她的行李里翻
出那根马鞭,她说她以前在阿根廷的牧场里常会骑马牧牛,所以一直带着这个指
望在外面也能有机会骑马,后来我发现用来抽她屁股也很合适。
「婊子,你不是喜欢玩儿这个吗?」我冷笑着,扬起鞭子,抽在她翘起的屁
股上。啪的一声脆响,她的身体一颤,屁股上立刻浮现一道红痕。她扭过头,吐
了口唾沫:「操你妈的,黄猴子!抽啊,使劲抽!老娘的屁股可不是给你这种劣
等种舔的,是给我皇威廉,凯瑟陛下骑的!」
凯瑟,又是凯瑟。她在床上一激动就喊这个称呼,搞得我像个替身一样。但
我没停手,鞭子一次次落下,抽在她白皙的臀肉上,红痕交织成网,她的长腿乱
蹬,丝袜被汗水浸湿,贴在皮肤上更显光滑。她的叫声从低沉的哼哼变成尖利的
浪叫:「啊!贱货!你这亚洲猪!抽死我啊!老娘的屁股是日耳曼的骄傲,你他
妈配碰吗?」
我扔掉鞭子,双手掰开她的屁股瓣,那粉嫩的菊花和湿漉漉的阴户暴露在空
气中。她已经兴奋的流水了,真他妈是个天生的贱货,阴唇肿胀着,晶莹的液体
顺着大腿内侧滑落。我的鸡巴硬得发疼,龟头直顶在她屁眼上,先是用力磨蹭,
我抓起枕头下的套子带上,伸进她的臭嘴里,用她自己的口水给我戴套的鸡巴润
滑,然后对着她的屁眼,一点点挤进去,真是又紧又舒服。「你这日耳曼母马!
现在还不是被我这黄种矮子骑在身下?张开你的贱屁眼,让我操进去!」
她尖叫着扭动:「不!滚开,你这蒙古杂种!老娘的屁眼是给白人贵族操的,
不是你这种黄皮猪!啊——!」我不管那么多,一挺腰,鸡巴生生捅进她的屁眼,
紧窄的肠道像火热的套子裹住我,她的身体猛地弓起,双手在身后挣扎着皮带的
束缚。痛楚和快感让她脸扭曲,泪水混着汗水滑落:「操!疼死老娘了!你这畜
生!拔出去!啊……黄猴子……操深点……不,滚!」
我开始抽插,粗暴地撞击她的屁股,每一下都顶到最深,她的叫床声断断续
续,夹杂着德语的咒骂,我听不懂,但知道她在骂我黄种矮子。我扇着她的屁股,
加快节奏:「叫啊,母狗!你的凯瑟呢?怎么不来救你这贱货?老子操烂你的日
耳曼屁眼,让你知道谁才是你的主人!」
她喘息着,屁股不由自主地往后迎合:「凯瑟……嗨,凯瑟……不,你……
你这矮子……操我……操死我……」她的声音越来越软,身体在我的撞击下颤抖,
我拔出鸡巴,套子上沾满她的肠液,我退下用过的套子,无套的鸡巴直接转战她
的阴道。那里更湿更热,我一捅到底,龟头撞上她的子宫口,她尖叫一声,整个
人瘫软下来:「啊!鸡巴……你的鸡巴……黄种的鸡巴……插进老娘的优等人的
子宫里了……真恶心!你这蒙古杂种!」
我骑在她身上,像野兽一样狂干,双手捏着她的奶子,拧她的乳头,她的长
腿缠上我的腰,丝袜摩擦着我的皮肤,带来阵阵酥麻。房间里回荡着啪啪的肉体
撞击声和她的浪叫:「操我!扇我!黄皮猪,你他妈的就这点本事?老娘在英国
时……啊!深点,操到子宫里,蒙古贱种!」
「闭嘴,婊子!」我吼着,鸡巴在她的阴道里搅动,抽插得汁水四溅,她的
阴唇被我操得外翻,红肿不堪。我又抽了她屁股几下,留下新的掌印:「你这日
耳曼骚货,嘴上骂我,心里却浪成这样?你的凯瑟操过你这么狠吗?老子要射进
你的子宫,让你怀上黄种的种,毁了你的优等血统!」
她大笑起来,笑声中带着哭腔:「射进来!你这劣等猪!老娘的子宫才不稀
罕你的低等精液……啊!要来了……操死我……凯瑟……不,你……我要你……」
她的身体突然绷紧,阴道剧烈收缩,裹着我的鸡巴像要挤干我。她高潮了,尖叫
着:「嗨!凯瑟!哦,奥丁啊……黄猴子……操我……我爱你……」
我也没忍住,猛地一顶,精液喷射进她的深处,她的身体抽搐着,我们同时
瘫软下来。她扭过头,红唇贴上我的脸,亲吻得又猛又急:「我要你……现在我
只要你……跟老娘回家吧,别让我一个人。」
她的吻带着咸涩的泪味,我的心软了,解开她手上的皮带,抱紧她高挑的身
体。她的长腿缠着我,乳房压在我的胸口,我们就这样纠缠着,汗水混在一起。
她喃喃着:「或者哪儿都行……只要跟你……别扔下我这日耳曼母狗。」
布伦希尔德休息片刻,爬起来把偷来的那瓶红酒喝了大半,脸颊飞起两抹羞
红,她懒洋洋地倚在床头,全身赤裸长腿交叠。她用脚尖挑起我的下巴,迫使我
抬头看她。
「告诉我,」她低声问,声音里带着酒意和一丝罕见的柔软,「你真的要跟
我走?离开中国?」
我平静的说:「我已经没什么可留恋的了。父母的坟我拜过了,弟弟选了他
的路,军队也要踢开我这块旧石头。不如干脆去你父亲在巴塔哥尼亚的那片旧庄
园。」
她盯着我看了很久,蓝灰色的眼睛里第一次没有了玩味和审视,只有一种近
乎孩子般的认真。
「可你知道吗?」她轻声说,「我其实很怕,我怕你有一天会后悔,我听说
中国人都很爱自己的家乡的土地。」
我爬上床,把她揽进怀里,闻着她身上混杂着红酒、烟草和淡淡汗味的香气:
「我也怕。我怕我配不上你,但我更怕的是,如果现在放手,我这辈子都不会再
有勇气去爱任何东西了。」
她忽然笑了,那笑声先是低低的,像雪地里远处的狼嚎,然后越来越大,带
着一点歇斯底里。她翻身把我压在身下。「那就别放手。」她咬着我的耳朵,声
音低得几乎听不见,「今晚不许想明天,不许想中国,不许想德国,不许想战争
结束后的全世界。就想我,只想我。」
布伦希尔德转过身去跪下,把自己的骚逼对我眼前,用自己的小嘴把我的鸡
巴,用她的小嘴舔的又硬了起来,然后再次转身跨坐在我身上,自己伸手扶着,
把我的鸡巴对准她的阴道口,慢慢坐了下去,开始自己上下活动,像个海妖一样,
要把我彻底榨干,但也让我舒服的欲仙欲死,这个娘们太刺激了。
几夜激情过后,我们都好好休息了几天,直到正月十六,国府的裁军遣散通
知和退休补助一起送到,我和美国领事馆申请后,计划和布伦希尔德一起搭乘美
国的邮政飞机,从北陵机场飞往天津,再转船去美洲。从北陵机场起飞时,我最
后看了一眼东北这片土地,今生我将永无机会再回来了。
……
这就是我所知道的,把我养大的祖父给我看的,可能是我父亲的人的私人笔
记,我不确定这个中国飞行员和布伦希尔德是不是真是我的亲生父母,但学校里
的人都说我有一种中国式的好学和勤恳。
当我追问后来发生的事时,祖父告诉我,他们两人在农庄住了没多久,就把
我留下,两人一起化名参加了阿根廷的南极科考队,死于突然降临的暴风雪中,
只有尸体被发现后运回安葬。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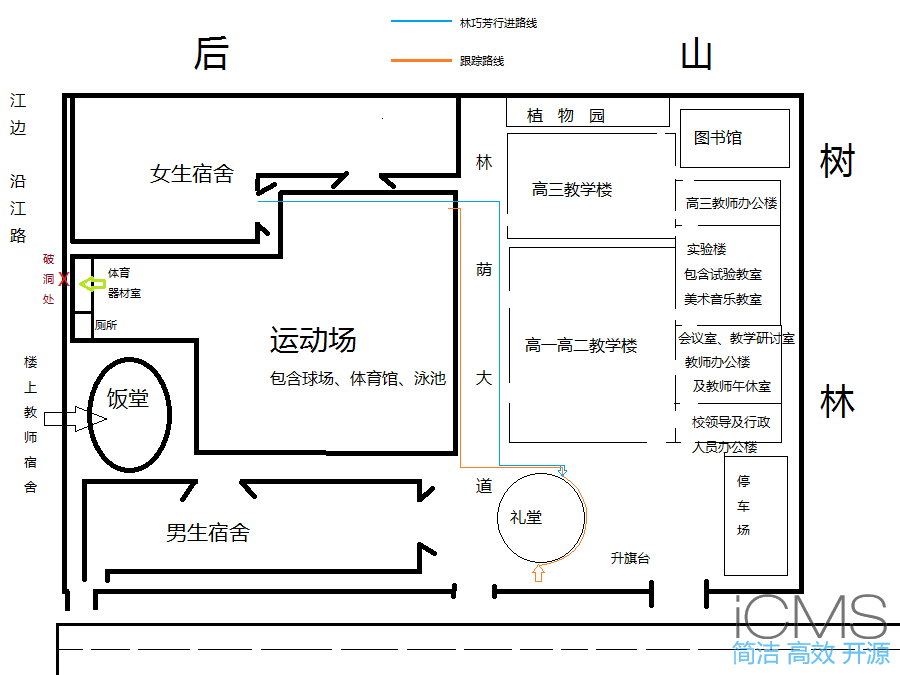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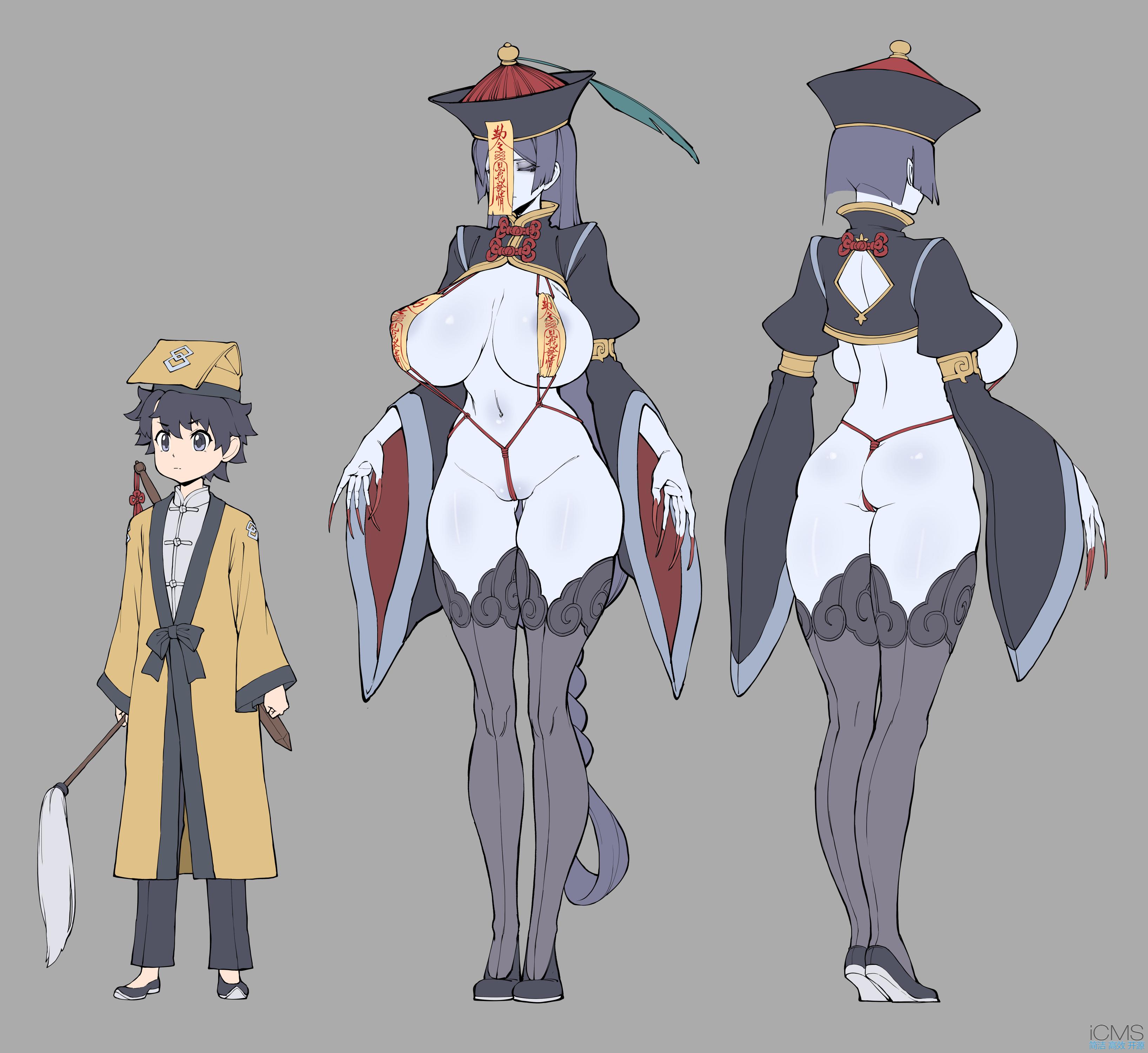

 加载中,请稍侯......
加载中,请稍侯......
精彩评论